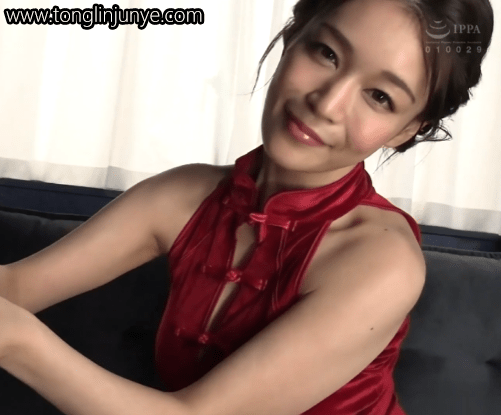吉瀬葵(Kise Aoi)第一次见到那个孩子,是在一个梅雨季快要结束的午后。她刚从殡仪馆出来,身上还带着一股消毒水和雨后的湿气。她丈夫——也就是那个孩子的父亲——在五天前车祸身亡,留下的除了银行账户里的一堆烂账,还有一个七岁多点的男孩,像捡来的似的,被丢在亲戚间转来转去,最后转到她手里。吉瀬葵没生过孩子,跟丈夫也不过是认识两年、结婚一年多点的“后妻”,很多人都觉得她会撇下那孩子不管,就像那个孩子的亲生母亲当初一样。但她没有。

她给孩子改了个名字,叫“悠人”,寓意是“愿你从此安稳行走,不再漂泊”。那时候的吉瀬葵是个脾气倔得要命的女人,别人越说她不能做的事,她越是咬牙去做。她给悠人买了新书包、新校服、新被子,把他安安稳稳地送进了那所小学,一边自己白天在药厂工作,晚上去学做便当。她其实并不喜欢小孩,特别是那种闷着不说话、眼睛一眨不眨盯着你的类型,但悠人就是那样。
最初的几年,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多余的对话。吉瀬葵像个严厉的管理员,每天按时提供吃饭、洗衣、睡觉的基本条件,悠人则像个被塞进规则里的小机器人,永远点头、低声说“谢谢吉瀬葵阿姨”,再也没有多的话。但她不是不知道他晚上有时候会做噩梦,小小的身体在床上缩成一团,背后冒着汗。她也不是不知道他在学校里被同学叫“没有妈妈的孩子”,有一整周不肯吃午饭,书包里藏着揉成一团的饭团。吉瀬葵也不是铁石心肠,只是她知道,一旦跨过那条线,什么都回不去了。

他们就这么相安无事地过了八年。八年,说长也长,说短也短,足够把一个七岁孩子养成一个十五岁的少年,足够把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推到快四十,眉眼之间多了几条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细纹。
那年的暑假,吉瀬葵带悠人去了她老家,那是一处废弃的铁道小站,站台早就没了,长满苔藓和蛇莓。她带着他坐在曾经她小时候跳格子的石板上,阳光从后山的缝里斜下来,像洒在记忆上的金色粉尘。她第一次对悠人说起自己的事,说她小时候差点被卖掉,是外婆死命抱住她的腿才把她留了下来,说她为什么从不让他叫自己“妈妈”,因为这个词对她而言太沉重,像山一样压在背上,一旦认了,她怕自己也被压垮。她说的时候没有哭,悠人也没有说话,但在那天晚上,他洗完澡,穿着宽大的睡衣走到她门前,站了很久,最终还是轻声说了一句:“我可以叫你妈妈吗?”
她没回答,也没开门,但眼泪却控制不住地从眼角滑下来,像久藏的雨水,终于找到了出口。
那之后他们的关系好像变了,又好像没变。吉瀬葵依旧是那个早起做便当、晚上打两份工的女人,悠人也还是那个规规矩矩、成绩优异的少年。但有些东西,就像溪流的走向,一旦改变,就再也回不到原来。吉瀬葵发现自己看他的时候,不自觉地想得更多——今天他有没有笑?为什么最近总盯着窗外发呆?他书包里藏的那封信,是不是哪个女孩写给他的?甚至连他多夹了一块炸鸡,她都能在心里细细斟酌:是不是长身体了?是不是压力太大想吃点安慰的?
这种心思,是从哪一刻开始变质的,连她自己都不愿承认。她只是意识到,有时候他放学回来晚了,她会紧张得坐立不安;有时候他不在,她会反复看冰箱里那罐他最喜欢的柚子果酱;有时候他走过来,她的心跳竟然会乱了一拍。她用所有理智去压制这些想法,甚至在墙上贴了“他是你的孩子”这六个字,每天出门前都要念一遍。
可惜感情不是理智能管得住的,特别是当那孩子长到十七岁那年,已经高高瘦瘦,眉眼间像极了她年轻时喜欢过的那个人。那年夏天,他们一起去打零工,在一个乡下的陶艺工坊,工坊的老板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,看着他们笑,说:“你们母子感情真好。”悠人轻轻看了她一眼,像是想说什么,又忍住了。回去的路上,蝉鸣刺耳,吉瀬葵走在前头,背对着他,却感觉得到那种沉默里的灼热,像炙热夏风中未说出口的情话。
真正让一切崩塌的,是悠人十八岁生日那天。他买了酒,说他成年了。吉瀬葵不肯喝,说他还没考上大学,不许庆祝太早。可悠人硬把酒塞到她手里,说:“我就想跟你喝一次。”他那天喝了很多,说了很多过去不曾说过的话,说小时候其实很怕她,但也很依赖她,说他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喜欢任何人,因为对“家庭”这个词已经死心了,但她改变了他,说他最希望的,不是叫她妈妈,而是希望她哪天能叫他一声“悠人,回来吧,我等你。”
她那天没哭,也没笑,只是把灯关了,说:“早点睡,明天还要上学。”但从那天起,她开始逃避,躲着他,换了工作,搬了家,甚至一度想离开城市。她知道事情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,可她还残留着那点作为“母亲”的理智,不愿成为一个“破坏者”。
可人心有时候就是这么吊诡。她越逃,悠人越追。到了最后,他们终于在那座她从不让他去的海边小屋重逢,那里是她过去唯一的秘密,是她曾经与初恋住过的地方。悠人坐在破旧的木椅上,手里握着她当年留下的日记本,里面每一页都写着他从七岁起的生活——他第一次感冒、第一次考第一名、第一次失恋,还有他第一次对她说“妈妈”的那一夜。
他读着那些字,眼眶发红:“你说你不是我妈妈,那为什么要为我写下十年的人生?”
她终于承认了,声音低得像海浪:“我不敢爱你,因为我已经太爱你了。”
影片的最后一幕,是悠人站在大海前,回头看了她一眼,而她终于走近他,一只手轻轻搭在他肩膀上。没有台词,没有拥抱,只有一滴泪,从她脸上滑落,和风中的盐粒混在一起,咸得发涩。
这部电影其实什么都没说透,可也什么都说清了。它讲的是一段无法命名的关系,一种越界的情感,它不是母子,却比母子更深;不是恋人,却比恋人更痛。它不煽情、不狗血,而是把所有的挣扎和纠结包裹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中,一点一点侵蚀你,让你不得不去问:如果爱一个人是错的,那坚持到底,是否还有意义?
也许答案不重要,重要的是,吉瀬葵最后选择不再逃。而我们每个人,在面对自己最不能触碰的关系时,又是否能像她一样,直面那份名为“爱”的困境?
那天之后,吉瀬葵没有再躲了。她回到了原来的城市,重新找回那份她曾经为了逃避而丢下的生活。只是,生活已经悄悄改变过轨迹,很多东西回不去了。邻居仍旧热情,但她总觉得别人看她的眼神有了点说不清的异样。悠人没有立刻回来,他去了北海道,说是要读一间风景很美的大学。她没拦他,也没追问,甚至没去送站,只是在他走的前一晚,把一个厚厚的便当盒放进他背包里,上面写着:“鱈魚味噌煮。你小时候不爱吃,现在也许会喜欢。”
她没有再提过那晚的对话,就像他们之间所有无法说清的情绪一样,被小心包裹起来,藏进心里最深最暗的角落。可她知道,那些话不是梦。她也知道,她做不到“理直气壮地拒绝”,但也无法“坦荡地接受”。就像她房间里那把关得紧紧的抽屉,谁都知道里面藏着什么,可谁也不敢轻易打开。
时间是个磨人的东西。它不会让人轻易遗忘,却会让一切慢慢沉淀下去。有时候她在煮味噌汤时,会突然想到悠人那双笑起来像她丈夫的眼睛;有时候听到谁喊了一声“妈妈”,她也会下意识回头。她还是一个人住,依旧早起,依旧做便当,只不过这次她学会了做两人份,然后把另一份封好,放进冷冻柜里,说不准哪天有人回来。
而悠人,也不是没回来过。大学毕业那年,他带了个女孩回来,女孩温温柔柔地说:“阿姨您好,我叫初音。”吉瀬葵笑着点头,说:“你们坐,我去给你们切点水果。”她动作熟练,甚至比以前更自然,但当她看见悠人看着初音的眼神时,那一瞬间心里涌上来的,既不是妒意,也不是怨恨,而是一种奇异的、放松下来的释然。
他有了自己的生活,也有了别人可以依靠的肩膀,而她终于不用再背负那份沉重到令人窒息的情感。他们像亲人,却也不只是亲人;像故人,却也从未真正成为陌生人。他们之间始终隔着一道无形的墙,那墙上布满了裂缝和伤痕,却始终没有完全倒塌。
电影最后一幕,是吉瀬葵在老屋的后院种下一株柚子树。那是她第一次亲手种树,动作笨拙却很专注。她穿着旧毛衣,膝盖上的泥巴一层又一层。种好后,她站起身,看着那棵小小的、还未扎根的新树,像是看着另一个“他”的开始。风吹过她的额发,她伸手抚了一下,忽然笑了。
那笑不是悲伤,不是悔恨,也不是释怀,而是一种近乎母性的温柔——她终于承认自己是那个“养他长大”的人,也终于学会放手让他走向自己的路。而那棵柚子树,就像她对这段关系最后的守候,不必言说,不必回应,只需静静站着,等风来,等果熟。
番号ROE-367是一部慢慢渗入你心里的电影,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,却用细腻到骨血的笔触讲述了一段最复杂也最真实的人性关系。它不试图给出答案,因为它知道,有些问题本来就没有答案。而它最动人的地方,不是情节本身,而是那份“敢爱又不能爱”的挣扎,那份“明明跨不过去却还站在原地”的执念。
看完之后你可能不会大哭,但在某个风大的夜晚、或者一个不小心喝醉的深更时分,你会突然想起吉瀬葵(Kise Aoi),然后心里某处软得一塌糊涂。因为你知道,你也曾在某段关系中如此小心翼翼地活着,像她一样,不敢靠近,却又舍不得放下。